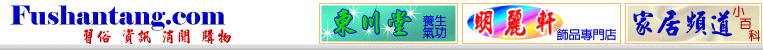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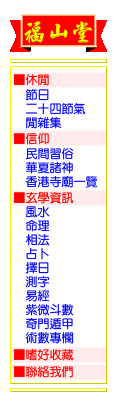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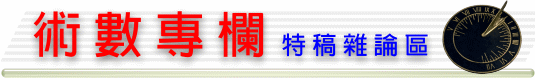
试析明代医易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 徐仪明
一
运用《周易》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医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这就逐渐形成了一门在易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的分支学科即医易学。按通常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援医入易已经初露端倪,至秦汉《黄帝内经》等著作就进一步吸取了《周易》中的阴阳观念、天人合一思想等。而从魏晋、隋唐到两宋,虽然易学研究(特别是两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易学家,但就医易学本身来说并无长足的发展。至金元时期,一些着名医家开始重视易学与医学的关系,如刘完素以易理阐发“火热论”,李东垣以易理来论说药性,朱丹溪以易理来讨论“君火相火”论,使医易学的研究成果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代,为医易学在明代达到极盛做了一定的准备与铺垫。
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能够达到极盛,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医易同源之说。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曾认为“凡欲为大医”,除了熟谙《内经》等医着外,“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还只是将《周易》作为名医知识结构中的一项内容,并未放在特殊的位置之上。而至明代,不少着名医家不在停留于泛泛地讨论医易关系,而能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医易同源的观点。孙一奎说:“《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期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认为只有将医易互参,明了太极之玄理,方能够随证用药应手而瘥。张景岳进一步将医易同源说发挥到极致。他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又说:“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人之情况,于象可验。病之阴阳,有法可按。”即认为易学乃是医学的指南,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都无非是阴阳变易之理,而此基本法则都存在《周易》一书当中。因此他又说。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不知《易》乎?”从而得出了“医易相通”、“医易同源”的结论。毫无疑问,上述孙一奎、张景岳的医易同源观念,是对千百年以来的医易关系问题做了高度的总结,也使医易学这一易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得以正式形成。其次,明代的医学家既有丰富的医学底蕴同时又具有十分深厚的易学修养。如张景岳学贯医易,其友叶秉敬在《类经》序中说:“世之能注易者,不出于程朱,能注内经者,不出于秦越人、王太仆。景岳一人,却并程朱秦王四人合为一人,而直接羲黄之脉于千古之上,恐非程朱秦王所能驾也。”指出张景岳学识渊博,兼通医易,超过或医或儒之人。张景兵医易学著作甚多,计有《医易义》、《大宝论》、《真阴论》、《太极图论》以及《阴阳体象》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医易学做了系统的论述,从而成为“医易学说”的真正确立者。其成就之卓著,影响之深远,可谓超迈前人。又如孙一奎着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以及《孙氏医案》等著作,无不贯通医易学的精神实质。史孟麟《赤水玄珠序》说:“孙君过余而论《易》,为究乾坤之元,探有无之极,若悬河泻水而莫可底止,盖从事于圣人之道者,将不得谓之通一乎。道亦惟其所适。孙君之于医,亦可谓一以贯之矣。将不得谓之医之圣者乎!”认为孙氏不仅能穷究易理而且能使之融于医理,因此誉之为“医之圣者”。孙一奎之于易学有着独特的造诣,也因之有家学渊源,“《易》之神,得孙子之先君子传也。……道遘异教家,秘之以岐黄术始察之消息升沉,寒暑虚实,而《易》之神,而神之胸臆间多矣”。而在《医旨绪余》一书中,孙一奎立有《太极图抄引》、《太极图》、《太极图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命门图说》等多篇医易学专论,颇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因此时人赞之曰:“东宿之于《易》也,深乎!……东宿之书,以随证用药终焉,其又得太极生生之用矣!夫一中为造化,而四时为迭运,此天地人同一太极生生之《易》也。”认为孙一奎对《周易》太极学说在医学中的阐发最具特色。再如赵献可,据《鄞县志》载,其人“尤善于《易》,而精于医”,著述颇丰,有《医贯》、《邯郸遗稿》、《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朱一例》等。其中《医贯》一书是其医易学的代表作,该书不仅将《易》理贯通于医理,而且能将《易》融汇于释家、道家等学说中,赵献可自己说:“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皆是物,一以贯之也,故命其书曰《医贯》。”《医贯》中尤以《论命门》、《阴阳论》、《相火龙雷论》三篇最具代表性,集中阐发了命门之“火”的作用,所谓“所重之先天之火”,因“火”象征了《易》之生生不息。另外,明代医家中还有不少人运用易学原理阐发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五运六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内容。如汪机的《运气易览》就是通过借鉴邵雍的象数易学来阐发五运六气学说之纲领,如其认为运用运气学说不应只限于一年一时,而应考虑百千年间运气的作用和规律,并以邵雍的元运会世说作为理论依据。再如王肯堂在临诊中十分重视气运对病症的影响,选药组方也很注重时令、气运,显示出他对易理的领悟。还有象张志聪以易学太极理论解释人体胚胎发育。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一些著名哲学家象王廷相、何瑭、方以智等人,既精通医道,又对易学有着深湛的研究,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明代易学与医学的高度结合。但由于他们的主要兴趣在易理本身,本文不拟对其做专门的讨论。
以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为代表的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被称为极盛时期,这是相比较于其它朝代而论的,金元以前医易学尚未有显著成就,而清代以降医易学渐趋式微。那么,笔者认为,只有将明代医易学与金元时期的医易学加以集中讨论,方能显示出明代医易学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从而可以看出其在中国古代医易学发展史上达到极盛的过程。
二
应该说,金元时期是古代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他们各创一说,相互争鸣,并从不同的角度援易入医,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明代医家在承继其学说的基础之上,又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当然绝非易事。然而明代医家凭借着深厚的易学功底,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使医易学达到了极盛的阶段。笔者认为,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突破了金元医家以易理比附医理或药理的方法,从而使医理得到易理的拓展,得出了新的理论结论。
金元医家多以《周易》之卦象比喻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药理。如刘完素首创“火热论”,即出之易理之“干阳离火”之说。而张从正则以《易》之卦象比喻人之器官,认为:“《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纲则眨,下纲则不眨,故《观》卦上巽而下坤。《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颌则嚼,上颌则不嚼,故《颐》卦上艮而下震。”以《观》卦为视之理,以《颐》卦为养之理,明显带有取象比类的特点。李东垣则以易象喻药理:“荷叶之物中央空,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为言说荷叶性动,易发散的性质,特援《震》卦之象以作例证。这些说法虽不无启发性,但仍然停留在一般性的模拟阶段,在认识程度上显得不够深入。
明代医家已不满足于医易之间的浅层认识,而试图以易理运用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进一步去探索人身的各种奥秘。张景岳认为:“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内外孰亲?天人孰近?故必求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先乎内而后可以及乎外;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其何以行之哉?”将易理作为深入探讨身心活动规律的理论指南。孙一奎则强调《周易》太极理论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医之为教,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及。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哉?”正是运用《周易》太极理论,赵献可、张景岳、张一奎等人在古代医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提出了太极命门说。而赵献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最具建树。
赵献可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极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穷其奥也。”即是说人体中的太极必有形迹可寻,而“人身太极之妙”即命门。“命门”一词最早见于《灵枢.根结篇》,但其未作详论。《难经.三十九难》说:“命门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仅说明了命门与肾有密切关系。而赵献可则直接提出了命门在人体中的具体位置,并绘出了图式。他说:“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七椎。……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命门在两肾之间,似《易》之有太极,位置虽很具体但无形迹。赵献可对此有所发挥。他说:“《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无极而太极。无极者,未分之太极。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一中分太极,中字之象形,正太极之形也。一即伏羲之奇一而圆之,即是无极。即曰先天太极,天尚未生,虽属无形,何为伏羲化一奇,周子画一圈,已涉形迹矣。曰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太极即无极,虽包含阴阳两仪,但属无形,因此时天尚未生,伏羲先天图画一奇,周敦颐太极图画一圈,已涉及形迹,但并非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开示后学而已。赵献可由此联想到肾非命门,人身之太极定非实物。他断定命门在两肾中间,无形迹可见。但此无形之命门则为生命的主宰,“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命门则为相火之源,“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但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因此,他认为命门为性命之本,即因其中有火的存在,“是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极”,而此火因其无形又寄托在左肾(水)右肾(火)之中。用易学太极理论来讲,就是无形之太极存在于有形之阴阳中。所以,赵氏在临证中,为使命门火强,则强调培补肾阴或肾阳。赵献可独创性地提出人身的太极为命门,其动力为无形之火,这是他运用易学原理于医学的一大贡献。他否定《内经》心为君主之说,另立命门为真君真主,在当时实属大胆设想。已故姜春华教授认为:“赵氏命门学说想象力高,说得具体,其所提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脑垂体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某些功能。”这可谓是通过易学太极学说的思维方法而得出的新结论,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价值。张景岳在此问题上,与赵献可如出一辙。他说:“命门具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孙一奎对此的认识与二人大同小异:“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火非水,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此动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亦无形迹。
显然,赵献可等人的太极命门说具有相当突出的理论创造性,在对易理的运用上超出了金元医家的水平。这说明明代医家开始自觉地以易理为认识工具去探索并解答医学上的未知问题,并取得了有一定价值的学术成绩,从而构成了明代医易学极盛的第一个显著特征。
第二,进一步深化了金元医家所关注的一些学术问题,并以争鸣和辨难的方式,使医易学研究走上更高的理论阶段。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曾提出过:“阳有余阴不足”的医易学命题。他说:“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为阴,天之在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也。”天为阳,天体比地球大,是阳有余;地为阴,地球比天体小,是阴不足。日为阳,恒圆而不缺,是阳有余;月为阴,虽圆而常缺,是阴不足。因此从自然现象看是阳有余而阴不足的。将自然现象模拟于人体生理状况之后,仍然处处可见阳有余阴不足的状况。但是,“阳”却变成了必须抑制甚至必须禁绝的东西。在朱氏看来,火属阳主动,肝肾“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而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这里的“阳有余”是指肝肾之中所存在的相火容易妄动,相火妄动就会使肾精流泄,又导致“阴不足”。并且天人相应,由于天大于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又因为日明于月,“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也可见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再加上“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最是难以长期持守,进一步使得阳有余而阴不足的状况更甚更烈。因此,朱丹溪认为要想不使此种状况发生,必须保持肾精的充足,这就要抑制相火,使之不得妄动。也就是说,如果要避免“阴不足”,关键在于不能出现“阳有余”的现象。
逮至明代,张景岳对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持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说:“尝见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谓人生之气常有余,血常不足,而专以抑火为言。且妄引《内经》阳道实阴道虚及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等文,强以为证,此诚大倍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以为丹溪之说歪曲了《内经》原意,因此,他提出了“阳非有余”论,与之针锋相对。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其着重阐述了阳气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从水火辨阴阳,他说:“水为阴,火为阳也;造化之权,全在水火。”说明水必须赖有阳气才能生物化气,所谓“天一生水”,就是说水赖天一之阳而生;火得水则降,水火相济则能生物。其二,从形气辨阴阳,其曰:“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说明“阳气”是人体的根本,没有阳气人就无法生存。其三,从寒热辨阴阳,他说:“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说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依靠阳光的热能,方可生长发育;因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显示出“热”能生万物,而“寒”则无生意。据此,张氏认为在阴阳之中,阳气是主要的。他说: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非阴能自盛也,阳衰则阴盛矣。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也由乎阳,非阳能死物,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
所以,张景岳在治则上主张应以温养阳气而填补真阴为主,在临床上主张惧用寒凉和攻伐之剂,他创左归饮治命门阴衰阳盛,右归饮治命门阳衰阴盛;前者意在峻补真阴,后者意在温壮元阳,所用主药均为熟地,结果被后人称为“张熟地”。张氏这种治疗方法有其独创之处,至今仍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尽管朱丹溪与张景岳的理论看上去水火不容,事实上却不尽然。朱氏认为君、相二火均属阳,因情欲所煽而易动,所以以养心寡欲为要,因为心静则不会为物欲所惑,而不致使相火妄动。其所谓“相火妄动”则为邪火,而不是真正的火,其言“阳有余”则为阳之邪,并非真正的“阳”。但朱氏却没有将其理论讲清楚,故造成这一聚讼百年的公案。张景岳所以强调贼人之火不是君相的真火,邪火与相火两不相涉,邪火方可言贼,而相火不可言贼。因此可以说,张景岳阳非有余,阴也常不足论,是对朱丹溪说法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认识。但由于其持论过于激烈,致使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学术局面。
由以上可以看出,明代医家是总结前人尤其是金元诸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的。他们凭借着深厚的易学底蕴,能够充分运用易学的整体性思考的特点,通过考察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各种方式,极力去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了新的富有创造性的理论结论。当然,并不能因此就说明代医家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毕竟使古代医易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将医易学推向了极盛的阶段。
三
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迥非寻常的学术思想原因的。前已论及,明代诸医家具有深厚的易学底蕴,但是这种易学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原因不能不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相关联。宋明理学的易学观念对于明代医易学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宋明理学初创开始,易学研究就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据《宋史.艺文志》载,仅北宋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深入发掘《易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总体上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并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宋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两大类型。象数源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和邵雍。周敦颐的易学著作为《太极图说》与《易通》。周氏接受释道之学,将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将“太极”作为混沌未分之元气,经过动静阖辟而分出阴阳二气,阴阳互动又生出五行,五行之气按顺序流布,方有春夏秋冬的交递。周敦颐的易学思想为象数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邵雍的易学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邵氏易学将《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与道教的宇宙生成说相糅合,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学的特色。他认为宇宙的本原为“太极”,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为绝对之“一”,在静止中产生“二”,“二”具有变化不测之性能即“神”,因此而生出“数”与“象”,并由此而有了有形的个体事物,其“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邵雍又有“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生”,即“道为太极”的说法。另外邵雍还有“心为太极”的观点。由于康节易学较为杂驳,后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贬之者认为其穿凿附会,褒之者认为其阐扬伏羲、孔子之道。其易学中的一些观念,对后世医易学的发展深有影响。义理派的代表人物张载与程颐。张载善于以阴阳二气解易,于《易传》中特重《系辞》,其易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阐释《系辞》来完成的。他在《正蒙.参两》中说:“地所以两,分刚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参,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以太极表示阴阳刚柔的统一。刚柔男女彼此对立,谓之两;对立又相互统一,谓之参。又说:“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还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两,有两一在,无亦一在。然无两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这里可以看出,张载所谓“太极”又与“太虚”范畴一样,二者都是将“气”的有无、虚实、动静等性质与状态统一起来。张载将《周易》的“太极”与《内经》的“太虚”相联系的说法,被明代张景岳所吸取与发挥。程颐解《易》不讲太极,而以“理”为最高范畴。他在释恒卦《彖》文“观其所以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时说:“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就是说日月能久照,四时能生成万物是因顺天之理(或道)。阴阳二气以阴阳之理为存在根据,有形之气只能顺其无形之理才能永恒存在,也即所谓“有理则有气”。程颐这种以理为本的观点多被朱熹所继承。
南宋朱熹为宋易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他主要继承发展程颐及张载的易学思想,以讲义理为主,同时又兼收邵雍的象数之学。朱熹以太极为其易学及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其释“易有太极”时说:“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又说:“阴阳只是阴阳,道是太极,程子说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太极就是理,就是所以一阴一阳的道。朱熹又提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之说。《太极图说解》云:“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又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是最高的理,此理又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人人物物都依据此理而存在,所以人人物物俱有此理。朱熹易学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讲论易理者,多兼及象数。
明代医易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阐发医学观点的时候,既以宋易的义理派思想为蓝本,又发挥宋易的象数学思想,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显示了明代医家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胸襟,这也正是明代医易学能达到极盛的重要原因。
先从义理思想观点来看。张景岳说:“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由是观之,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即以太极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本原。其中所引《太始天元册》中文,见《素问.天元纪大论》。而将《素问》所说“太虚”等同于《系辞》所说的太极,明显受张载的影响。在他看来,以“太虚”解释太极最为合适,因为“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为一,是名太极”。当然,这里所谓的太虚与张载所论也不尽相同,因其“自无而有”。他又说:“太虚者,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故曰太虚。”太虚又可看作周敦颐的《大极图说》中的太极本无极。并明确指出太极即朱熹所说的“理”,“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之具”。由此看来,张景岳所谓太极是指精神性的本体。但是他又说:“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似乎又以太极为阴阳二气未分之统一体。在《类经图翼.运气上》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如“先天者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这种说法又将太极解释为物质性的气。由此可以看出,张景岳的太极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同样的矛盾也见于朱熹易学思想中,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作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当他讲到太极即气而化生万物时,明显受到张载元气宇宙生成论的影响。而当其讲到世界本原时,理即太极与气即为一种主从关系,如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这种宇宙生成论与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在朱熹思想中始终存在,使理和气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张景岳太极理论中的矛盾状况与朱熹的十分相似。然而张氏将太虚说与太极说密切结合在一起,使医易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由于明代朱熹理学已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其易学思想在明代诸医家中影响颇深,孙一奎《医旨绪余》中的观点也多从朱熹处加以发挥。其《太极图抄引》说:“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故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夫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之一物耳,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朱熹有所谓“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即是说“万个”事物之理,全具“一个”本体之理。孙一奎依据这种观点,讨论太极与万物即“一”与“多”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阴阳五行还是人或物都存在着太极之理,但太极之理也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其说:“天地间非气不运,非理不宰,理气相合而不相离也。何也?阴阳,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理也。理者,太极也,本然之妙也。”显然其发挥的为朱熹宇宙生成论方面的内容。宋易义理之学特重思辨,“牛毛茧丝,无不辨析”,这种特点使得明代医易学哲理化的致思倾向十分明显,理论深刻性与严密性都超过了往代。
在对宋易象数学吸取的过程中,明代医家尤为看重邵雍之学。邵雍着眼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万物的分衍过程,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这一思想为张景岳所吸取。张氏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并进一步作了发挥,其云:“所谓一分为二者,是生两仪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与阳,两仪立焉。是为有象之始,因形以寓气,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有象之祖也。医而明此,乃知阴阳气血,皆有所钟,则凡吾身之形体气质,可因之以和其纯驳偏正,而默会其禀赋刚柔矣。”这是以一气化分的原理阐述人体阴阳气血、形体气质形成的过程。张景岳还对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等等道理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不出邵雍“加一倍法”的范围。他在讨论运气学说中更以邵雍之说为张本。其云:
邵子曰: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数之中者,五与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为生数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为成数之主。天元纪大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是以万侯之数,总不离五与六也。而五六之用,其变见于昭著者,尤有显证。……惟是数之为学,圆通万变,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悉秋毫。
这里的“五”与“六”两个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气象预测学,而且宇宙间万事万物,千变万化都可以用之来加以推算,这是因为“以五而言,则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谷、五畜之类,无非五也。”“以六而言,则天有六合,岁有六气,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吕、六甲、六艺之类,无非六也。”所以上至苍天,下至黄泉,大如元气,小如毫末,都不能逃出数之外。如果以数来观天地,天地也不过数中之一物。仅观张氏此论,俨然是一位象数派的易学家,将数的地位与作用推向极端。由此也可以看出,邵雍在医易学领域中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象数学容易与医学中固有的数学知识相发明,明代医家多因此而崇拜他,如张景岳说:“数之为学,岂易言哉!苟能通之,则幽显高下,无不会通,而天地之大,象数之多,可因一而推矣。明乎此者,自列圣而下,惟康节先生一人哉。”当然,象数学派对明代医易学的影响固然极大,但其是否都属于正面的作用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议。有论者认为邵氏易学用数所构造的世界模式,抹煞了数的客观性,造成明代医易学具有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气息。但是,明代医易学中蕴涵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认识则是值得予以肯定的,这些方面又不能承认是邵雍象数学对医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显然,明代诸医家的努力最终使医易学形成了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的易学分支学科,集中了宋代易学两派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和思想观念,标志着中国古代医易学达到了峰巅状况,为中国古代易学史、哲学史乃至医学史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