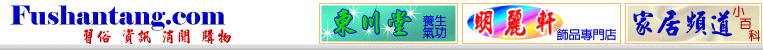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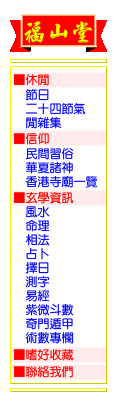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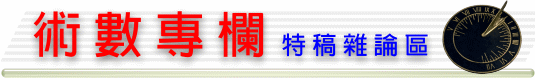
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 余欣撰《敦煌学辑刊》
摘要:
本文重新校录了上博48册《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文》,并以此为核心史料,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传统文献,对唐宋时代敦煌的墓葬神煞进行了考辨。试图不仅恢复敦煌万神殿中这些重要神祇的“席位”,而且揭示民生宗教的神灵信仰体系中这一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远远超出松散型宗教中其它类别的神祇,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
1993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很多重要的资料首次刊布。其中最富研究旨趣的当属上博48册子本中抄录的《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文》。郝春文先生独具慧眼,录出全文并对研究前景做了四个方面的提示:首先,为确定曹议金卒年提供了新证据;其次,记载了曹议金的入葬日期,并为探寻曹议金墓地提供了线索;再次,还可引发人们对曹元德、曹元深的执政情况作进一步考察;最后,为研究敦煌丧葬祭祀习俗和曹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新材料。可惜的是此文发表以后,却并没有引起敦煌学界足够的重视,迄今尚未有人对本件文献作更深入的探讨。因此笔者拟在郝氏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文献的性质进行界定,并对所祀诸神,主要是墓葬神加以考察。先以文书原件影印本为底本,郝氏录文为参校本,将本件重新录文、标点如下:
维大唐清泰四年岁次丁酉八月辛巳朔十九日己亥,孤子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谁(谯)郡曹元深等,敢昭告于后土地神祇、五方帝、五岳四渎、山川百灵、廿四气、七十二候、四时八节、太岁将军、十二时神、墓左墓右、守大夫、丘承(丞)墓伯、四封都尉、魂门停(亭)长、地下府君、阡陌、游击、三丘五墓、家亲丈人。今既吉辰良日,奉设微诚,五彩信弊(币),金银宝玉,清酒肥羊,鹿脯鲜果,三屠上味。惟愿诸神留恩降福,率领所部,次弟就座,领纳微献,赐以嘉福。主人再拜,行酒上香。奉请东方苍龙甲乙墓左之神,奉请南方朱雀丙丁墓前之神,奉请西方白虎庚辛墓右之神,奉请北方玄武壬癸墓后之神,奉请中央黄帝后土戊己墓内之神,奉请乾坤震巽离兑坎艮八卦神君,元曹、墓典、墓录、墓鬼、殃祸、墓秏(耗)之神,童子、宝藏、金印、金柜(匮)、玉信、黄泉都尉、蒿里丈人,一切诸神等各依率所部降临就位,依次而坐,听师具陈。主人再拜,行酒上香。重启诸神百官等,今既日好时良,宿值天仓,主人尊父大王灵柩,去乙末年二月十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兆,修荣(营)坟墓,至今月十九日毕功葬了。当时良师巽择,并皆众吉,上顺天文,下依地理,四神当位,八将依行,倾(顷)亩足数,阡陌无差,骐(麒)蹸(麟)、凤凰,章光、玉堂,各在本冗,功曹、传送,皆乘利道,金柜(匮)、玉堂,安图不失,明堂炳烛,百神定职。加以合会天仓,百福所集,万善来臻。又恐营选(造)之日,堀(掘)凿筑治,惊动地神,发泄上气,工匠不谨,触犯幽祇。或侵阴阳,九坎八煞,非意相妨,或罗天纲,或犯魁罡,或惊土府,或越辛(胜)光,或逆岁时,横飞祥。今日谢过,百殃消亡,死者得安,生者吉祥。苍龙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尊前,玄武御后,宝藏金柜(匮),四方日益,〔百〕官崇利,公侯卿相,世禄不绝,所向休泰,永保亢吉。尚飨!主人再拜,行酒上香。主人某乙等谨复重启,所献微礼,蒙降福佑,愿镇谢已后,亡者魂神,安宁幽室,生者兴崇,子孙昌盛,长保嘉庆,内外贞吉,福善日臻,祸殃休息。殷勤奉谢,庶士(事)如法,薄礼虽轻,微意实重,既蒙慈泽,领纳丹诚,上下诸神,尽情幸乐,皆为醉饱,三爵既固,福崇嘉庆。今日直(值)符、直(值)使,前后游击,邪魅驱逐万里,阡陌、将军、亭长、都尉,卫护幽宅,永保贞吉,丘墓安静,子孙富贵吉昌。既昭周流,宣祭已毕,时多味歇,请收余祚。尚飨!便酌酒与主人寿福及散洒四方。又取酒祝曰,今蒙福佑,愿亡灵幽室,永无灾难。饮酒讫,再拜。又重请三王之礼,悉以周遍,镇谢之福,收藏已讫。合座饱满,上下喜欢。时延日暮,不敢稽留,坐者既疲,立者复劳,酒冷无味,肉冷无气,愿神严驾,各还本位。在左还左,在右还右,上官还天,下官还地,垂恩纳佑,勿令故气邪精,横相扰,所恶气,远驱万里,子孙安吉,永无后难。上下再拜,送神上路。谨以终始,再拜。
一、《曹元深祭神文》的性质
郝春文认为“太岁将军”、“苍龙”、“白虎”之类,源于道教,还有一些名目虽然暂时未能考出其源流,但从其名称看,很可能也与道教有关。因此,这篇祭神文透露出曹氏家族在尊儒崇佛的同时,也信奉道教。我们对归义军时期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有重新认识的必要[3]。对此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这些神煞和仪式未必就是属于道教的,而有可能代表了更源远流长的中华本土鬼神信仰及生死禁忌。我们先对《祭神文》的性质略作考索,但侧重点将落在郝氏未考的墓葬神煞上。
宋代王洙等所纂集之《地理新书》,年代稍晚于《曹元深祭神文》。在卷一五《送葬避忌》中有“五姓墓内神祇方位傍通”中,列有宫、商、角、征、羽等五姓的墓内神煞所在十二地支方位表,并有一段文字说明若触犯这些神煞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及祭神所带来的好处。现略去表格,征引表后文字如下:
右,青龙,犯之,三年内害家长及子孙;朱雀,犯之,主县官文书、公讼争斗;白虎,犯之,主年内害子孙;玄武,犯之,散失钱财,盗贼,凶;宝藏,去墓九尺,主横得钱财物,吉;中冢,犯之,大凶;金匮,向而祭之,得财帛,进益,吉;金印,去墓九尺,主富贵;向而祭之,吉;玉信,去墓九尺,主富贵,向而祭之,吉;丈人,去墓十二丈,犯之,主贫困,少子息;丘丞,犯之,令人颠狂,暴死;墓伯,犯之,令人暴死,后代不利;童子,犯之,主多病、无子;元曹,犯之,主暴死;墓录,犯之,主县官斗讼;墓典,犯之,主多病;墓耗,犯之,呼人口,大凶;殃祸,犯之,主百日外害人口;墓鬼,犯之,大凶。
《祭神文》中的墓葬神煞几乎在《地理新书》中都可以找到,为曹元深为何要祭祀这些神煞提供了注脚。但是要彻底弄清楚文中诸神煞,必须先确定《祭神文》的性质,而这一点需要联系东汉以来的墓券(买地券)和墓中陶瓶上的镇墓文方能解决。先征引一件典型的墓券以供参照,《东汉延熹四年(161)九月平阴县锺仲游妻墓券》:
延熹四年九月丙辰朔卅日乙酉直,闭。黄帝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墓左墓右、主墓狱史、墓门亭长,莫不皆在。今平阴偃人乡苌富里锺仲游妻薄命蚤(早)死,今来下葬,自买万世冢田,贾直九万九千,钱即日毕。四角立封,中央明堂。皆有尺六桃卷(券),钱布铅人。时证知者:先□(世)曾王父母□□□氏知也。自今以后,不得干□(扰)。主人(以下背)有天帝教,如律令。
这是现存最早的一件镇墓性质的墓券。由其行文款式已大体齐备,可以推想此类范式的形成应当更早。《曹元深祭神文》中的墓葬神煞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型,甚至有些直接对应。这些具体的神煞,下文再作考述。我们再引录一件和《祭神文》同时代的《后蜀广政十八年(955)十二月眉州彭山县宋琳地券》:
维广政十八年太岁乙卯十二月乙亥朔二十日甲申。大蜀国眉州彭山县乐阳乡北通零里殁故宋琳地券。然琳生居郡邑,死安宅兆,昨去十月二十三日倾背,今葬协从。相地袭吉,宜于上代营内庚地,置造□宅。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内方勾陈,分掌四城(域)。丘承(丞)墓陌(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阡(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若辄有犯诃禁者,将军、佰(陌)长付河伯。今用酒脯钱财,共为信契。财地交度,工匠修营,永保求(休)吉。知见人岁月主者。保人今日直苻(符)。故气邪精,不得吝。先有居者,各去万里。如为(违)此约者,地府主吏,自当期祸。主人内外,存亡安吉,一如五帝使者女青召(诏)书契券。急急如律令。
这件地券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解决《祭神文》的性质问题很有参照价值:首次出现用酒脯钱财祭祀地下诸神吏作为盟信。在其它墓券中,信契的建立是依赖于这两种手段:其一是声称此地是以多少多少钱从地下诸神那儿买来的。虚拟的钱币常动辄云数万,无非是想表明这是一桩合法的买卖,其所有权不得任意剥夺。其二是假借最高神的名义下诏书、符册给阴间所司,诸神必须奉勅执行。文中的语句都包含着命令、警告的口吻。经常被借用的神有黄帝,如《锺仲游妻墓券》;有黄神,《东汉熹平二年(173)十二月张叔敬镇墓文》:“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有天帝,如《东汉某年(二世纪)刘伯平镇墓券》云“执天帝下令,移雒东乡东郡里刘伯平”,《唐某年(八世纪)许州扶沟县赵公达及某氏镇墓券》称“天帝告”;也有以“天地使者”的名义,如《东汉阳嘉二年八月曹伯鲁镇墓文》:“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央(殃)去咎”;有太上老君,如《南齐永明三年(485)十一月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宋武陵王前军参军事刘觊镇墓券》云“太上老君符勅”、“一如泰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神太上老君陛下女青诏书律令”;有五方帝,如上文《宋琳地券》云“五帝使者女青召(诏)书契券”,《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六月庐州合肥县姜氏为亡妹买地券》云“急急如五帝使者书律令”,《南宋淳佑三年(1243)七月福州怀安县赵与骏妻黄氏买山券》云“五帝使者奉太上勅,急急如律令”。从来源上看,都是中国本土的信仰,而从时间上看,大致是汉代为天帝、黄帝或黄神,他们是上古时期就已形成的最高神。索安认为他们是在汉代民间信仰的多样传统和背景下,对同一个最高天神的不同称谓,黄神即黄帝,表明阴间主司和死者的归属不限于太山和蒿里,这一职能已扩大到整个五岳。道教兴起的南北朝则是太上老君,五代十国以后多为五方帝。但是这种时代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十国时期还用天帝或太上老君的例证也不是没有,如《南汉大宝五年(962)十月内侍省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曰“神仙若问何处追寻,太上老君勅青诏书,急急如律令”。如果我们将以上这两种手段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威逼利诱”。
但是,在《宋琳地券》中出现了另一种手段,即以酒脯钱财祭祀诸神,这既是一种交易,甚至可以说是对神的贿赂,也是一种盟信仪式。目的是想让诸神按照人的意志尽忠职守,护卫亡灵,“阡(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这种做法也被以后的买地券所继承,如《金明昌二年(1191)七月河南府洛阳县赵通买地券》:“今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时(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安厝,已后永保休吉。”由此件买地券可知,这种祭祀地下神吏的仪式用的是太牢,规格较《宋琳地券》为高,而与《祭神文》相等,只是《祭神文》表述得更为明确:“奉设微献,五彩信弊(币),金银宝玉,清酒肥羊,鹿脯鲜果,三屠上味。”
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的几件《唐祭五方神》残片,提供了更为关键的信息,表明这种祭祀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因此,它的发轫是与买地券同时代的,祭祀仪式与买地券存在着密切的连带关系。现征引相对较为完整的一件残片如下:
]〔西〕方白帝白〔招据〕, [ 〔兽〕白虎□神□〔威〕振怒,赤娥若鸟,玄无所犯,此〔诸神〕死鬼怖。其某甲死鬼无系属处,故书名字,□□方神,愿为禁摄,莫史(使)犯人,速摄囚。主人再拜,酌酒行〔伤〕(觞)。敢告北方黑帝协纲纪,恒山之神兽玄武,□神玄冥,难恶处,飞惊千里憎(层)冰固。 ]其某甲死鬼。 ]〔方〕神速。 ] 〔北〕方神速。 ]〔莫〕使犯人,生死路别,不得相亲。 ]付北方神,速摄囚,主人再 ]〔拜〕,[
刘昭瑞指出,这件文书反映的内容是镇墓活动,这类巫、道迷信,类似于道教科仪中的“醮墓仪”。此文书虽然出土于唐墓中,但语言和表述的观念都比较古老。反映死生有别这种生死观的镇墓材料,据内地考古所见,盛行于东汉,南北朝时已极为罕见,隋唐时已完全绝迹。上举醮墓文书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很可能直接来源于东汉。至此,我们可以比照买地券和《唐祭五方神》,对《曹元深祭神文》的性质作如下的推断:曹元深在曹议金下葬之后,举行醮墓仪式,以作动土触犯神祇的谢罪及将来护佑之功的酬答,或许还兼作买地的证盟,即地券中所谓“用酒脯钱财,共为信契。” 《祭神文》就是专用于这一仪式上宣读的祈愿文。“勿令故气邪精,横相扰,所恶气,远驱万里,子孙安吉,永无后难”云云,表明唐宋时代人们信仰中的生死异途,死者魂神不得相注的观念虽已淡化,不再是醮谢的主要目的,但仍有一丝痕迹残存。
此外,《宋琳地券》写于前蜀时期的眉州,引发我们对敦煌下葬之后祭地府诸神仪式的来源的思考:是否由蜀地传入?拙文《唐宋之际敦煌妇女结社研究以一件女人社社条文书考释为中心》中,有一小节对以往有关敦煌与四川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敦煌的“走桥”风俗有可能源于蜀地的看法。现在《祭神文》的研究,似乎又为两地间的关系增添了一条新的例证。
二、《祭神文》中诸神的分类
《祭神文》中开列的诸神名单,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其实是有内在依据的。要解释这个问题,也必须溯源至汉代的镇墓文。《熹平二年张叔敬镇墓文》: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狸(埋)。眉须(须)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就整个镇墓文的性质和形式而言,是作为死人的阴间通行证,颇类似于汉代的“传”,或者说“过所”。吴荣曾指出:“文中常用‘谨告’、‘移’、‘令’等字眼,文末则用‘急急如律令’或‘如律令’作为结束语。这是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但多数的文句押韵合辙,却又和文书不同。”本件镇墓文中,“告”和“移”这两个文书术语的使用也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们将天帝使者所要传达命令的对象作了层次上的区分。“告”是天帝使者直接下达命令给负责守护张氏墓的神祇。“移”是次一级传达,他们的关系稍间接一些,是对墓中死者有管辖职权的阴曹官吏。
相应地,《曹元深祭神文》也大致作了一下诸神等级的区分。但因为所祭祀诸神的座次要依照神的等级排定,所以和《张叔敬镇墓文》的次序刚好相反。第一次奉请的神级别较高,相当于《镇墓文》中“移”的对象,“主人再拜,行酒上香”之后第二次奉请的级别稍低,相当于《镇墓文》中“告”的对象。分两次祈愿,可能是买地券依然划为两个层级的反映。可惜曹议金墓没有发掘,买地券是否真的作此区分难以确知。当然,《祭神文》的等级界限并不是很严格,第一次奉请的混入了魂门亭长,第二次奉请的大多是墓内之神,但黄泉都尉和蒿里丈人却又厕身其间。
如果仔细分辨,第一次祈愿的还可以两个层次分地上神和地下神,地上神又可分为两组:后土地神祗、五方帝、五岳四渎、山川百灵可归为“空间神”,廿四气、七十二候、四时八节、太岁将军、十二时神可冠之以“时间神”。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命运观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的行事是否与宇宙(时空)运行的恰当的坐标点相合。一切占卜术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祭祀这样的大事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要将这些“时空神”放在首要的位置。下葬之后要祭祀“时空神”,也在南朝就已初露端倪,《南齐永明三年刘觊镇墓券》在地下神煞之前就列有“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帝?)后土”。
三、墓葬神煞
墓葬神煞中有些是习见之神,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八卦神君等,有些则浅显易晓,如墓鬼之类,自可略去不谈。为免烦琐,以下仅就一些较为特殊的做一些简单的考索。
1、几个重要神煞的考释
(1)丘承(丞)墓伯
《祭神文》中作“丘承墓伯”,以为丘承乃墓伯之名。其实“承”为“丞”之同音兼形近误字,当作丘丞、墓伯为是。丘丞始见于《东汉延光元年(122)镇墓文》:“生人之死易解。生自属长安,死人自属丘丞墓。”王育成认为,与“长安”句相对应的不是“死人属太山”或“东太山”,却是“死人属丘丞墓”,这反映出泰山治鬼的迷信在此时或没有产生或虽产生但还没有进入解除术中。笔者赞同此观点。因此,丘丞可以说是形成最早的一个墓葬神煞。丘丞、墓伯均可单独使用,两者经常并列,有两个原因:一、人死入墓,墓穴于山,丘墓连书,合乎逻辑,故《永明三年刘觊镇墓券》合而言之称“丘墓之神”;二、为了押韵合辙。所以两者顺序可置换,亦可单用,各举一例如下:《吴永安五年七月丹杨郡石城县校尉彭卢买地券》:“谨请东陵西陵暮(墓)伯丘丞,南(陌)北(陌)地下二千石,土公神□。”《晋某年(四世纪)程氏葬父母镇墓券》:“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门伯史、蒿里父老。”武周时期,丘丞还分置左右二员,如《武周延载元年(694)八月润州丹徒县伍松超买地券》即作“左右承(丞)、墓伯”。“丘丞”误为“丘承”,皆见于隋以后之买地券,现知最早一件为《隋大业六年(610)二月长沙郡临湘县陶智供买地券》,表明这一混淆大概始于隋唐之际。丘丞,乃模仿令丞之类人间官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墓伯”却略为复杂。在《东汉某年刘伯平镇墓券》中称为“墓父”。“伯”、“父”,当为父老之称。韩森认为,虽然地下官僚体系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并非完全是汉代官僚机构的镜像,因为“伯”就不是官号而仅仅是尊称。但是似乎也不尽然,譬如《熹平二年张叔敬镇墓文》“东冢侯、西冢伯”,《东汉熹平元年十二月陈叔敬镇墓文》(三件)则分别称为“西冢公伯”、“北冢公伯”、“东冢公伯”,显示也有步入官僚化的轨道的例子存在。神鬼名号常以世俗官僚为蓝本构拟,本宗教信仰之通则之一,以下墓葬神煞亦多循此例。但诚如本章第一节所强调的,官僚的科层体制并非是神祇等级的唯一参照系,同样,也未必是神祇名号唯一的来源。不论“墓伯”是否来源于官号,丘丞、墓伯之身份均为掌管亡人灵魂的地下官吏,是没有问题的。
(2)四封都尉
“四封都尉”盖即由《程氏葬父母镇墓券》中的“地下都尉”演变而来。“四封”当指墓之封泥四至,即《光和二年十月王当等买地券》所谓“四角封界”,而在《延熹四年平阴县锺仲游妻墓券》中称为“四角立封”。“四封”既可实指整个坟墓的占地范围,又可虚指想象的空间,如《永明三年刘觊镇墓券》所云:“封域之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上极青云,下极黄泉。” 四封都尉肩负守护职责的辖区可真不小。
敦煌当地的发掘的墓葬中,除了较为常见的青龙、白虎等四神以及方相外,未能发现其它墓葬神煞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全国的墓葬壁画、画像石等考古出土遗物,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图像学数据的。在河南南阳地区的冯儒人墓棺床后侧和紧挨主室的藏阁中曾出土一画像石,其第15号为墓中唯一的阴刻画像,为以脚踏强弓的武士形象,发掘报告称之为“蹶张”。朱青生反对这一解释,他怀疑是将军门神。其实类似的武装守护神形象南阳汉代画像砖石中有许多,我认为门神似乎不应该刻在这个地方,与其说是门神,倒不如看成四封都尉更为合适。此外,朱青生把汉画像石中的将军形象全部解释为将军门神,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目前不可能将这些将军所代表的神祇一一加以指认。
(3)墓门亭长与魂门亭长
魂门亭长几乎出现于所有买地券和镇墓文中。魂门或曰魄门是假想的灵魂升天之门,所以亦称“天门”,不能将其与实际的墓门等同。这在《大业六年陶智供买地券》中区分得很清楚:“魄门监司、墓门亭长”。姜生认为,阙即“魂门”,汉墓墓砖、石棺上多刻有阙,而地面墓葬附近也往往以砖或石建阙,这些阙都是用来引导死者从地下世界上升到天上仙界去的引路标帜。考古材料中的“门亭长”即“魂门亭长”。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试作如下辨析。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前室南壁墓门西侧绘一人,佩剑,面向门,拱手弓腰,作迎送状,榜题“门亭长”。这是墓门亭长,而不是魂门亭长。
魂门概念应当与道家思想有关,汉代《西岳神符刻石》:“(符文)西岳神符,金丽之精,其斧钺积石岩,位在西岳参柭(?)之旁。灭(?)鬼百适,及为三形,魂以下臧,魄归寒泉(?)。其日正祭百神,□以除灾□,定死人名,魂门主之,乃为三精,急急如律令。”以前,因为把画像砖石上的阙和立在墓前的阙一视同仁地看待,因此均被当作墓主生前官阶和地位的表征。但是无法解释为何这样的画像砖石也有不少出现在平民的墓中。新材料的出土,迫使人们修正这一观点。1988年1月,内江市和简阳县文物部门对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进行清理,在简阳三号墓发掘出一具有15处榜题的石棺,其右侧中部,刻有双阙,阙顶一对凤凰昂首对立,榜题铭文曰“天门”,确凿地表明双阙即是天门之象征。高文对此遗物之价值给予高度评价:“‘天门’一语道破文物考古中对墓室浮雕的性质和功用的争论,它不是人们常说的表现墓室主人地位显赫的象征,也不是墓室主人身份的表白,而是通往天堂世界的大门。”而此前赵殿增、袁曙光已全面搜罗四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有“天门”榜题的鎏金铜牌和画像砖石,对此作了透彻的解说,阙为天门,画像所表达的主题是经天门升仙的思想,可成定论。但是,两位作者认为以前依汉代史书及题刻称之为“亭长”、“门卒”是错误的,应该定名为“大司”。最近,罗二虎又继承赵殿增、袁曙光的观点,对此作了更细致的阐述。但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其一,这是孤证;其二,“大司”的释读是否正确,本身尚有疑问;其三,“大司”的位置在左阙与白虎之间,而此图像上方已有榜题“天门”,因此“大司”不能认定是阙中人物的榜题。因此笔者认为仍应该是魂门亭长为宜。魂门亭长的基本特征是持盾立于阙旁,周进所云手持一物,即盾牌。吴曾德最早提出,手中持盾是亭长的职务标帜,但是由于他把亭长当作现实世界的小吏,又认为石刻、砖刻上的执盾者大多不能看作亭长,因为亭长不会是某一家的守门官。其实把这个形象理解为魂门亭长,就不会有此疑惑。考古材料所见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一型是双阙中间站立一人,戴冠,宽衣博带,手捧盾牌,作拱手迎接状,属于这一类型的除简阳石棺外,还有郫县新胜公社东汉墓石棺、彭县等地新收集的画像砖、泸州第13号石棺、新津崖墓石函刻石、富顺化肥厂汉墓石棺;二型为双阙左右各有一亭长对立,亭长形象与一型类似,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彭山县双河乡崖墓石棺、彭山县凤鸣乡蔡山村汉墓画像砖、乐山肖坝石棺;三型则是单阙左右各立一亭长,较为少见,仅知有泸州11号石棺;四型也不多见,现知标本为四川省博物馆藏成都郊区扬子山二号墓出土石棺,正中浮雕一重檐单阙,两旁各有一人躬身而立,左者执棨戟,右者捧盾,当为亭长。由以上考述可知,尽管经历从汉到唐的漫长历史进程,但是魂门亭长的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宗教意识中。只是因为唐代已不再流行在墓葬中使用画像石,所以只保留了魂门亭长的信仰,而形象已经泯灭了。
(4)蒿里丈人
蒿里是死人的归宿。在买地券、镇墓文、墓志铭以及古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故挽歌即有以蒿里命名者。例如《夏承碑》云:“中遭冤夭,不终其纪。夙世霣祚,早丧懿宝。抱器幽潜,永归蒿里。”《大业六年陶智供买地券》云:“年命寿尽,当还蒿里。”汉焦赣《焦氏易林》卷四:“豫:病笃难医和不能治,命终期讫,下即蒿里。”晋崔豹撰《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用二章。……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唐代,蒿里为灵魂居所的观念仍在社会各阶层中流传。张说《大唐祀封禅颂》:“其中垂白之老乐过以泣,‘不图蒿里之魂复见干封之事’。”著名诗人骆宾王、李白、杜甫皆有相关诗作,兹不具引。在敦煌,这一观念还通过类书广为传播。敦煌类书《语对》云:“蒿里,死人里也。”
前野直彬提出,“蒿里”即《汉书.武帝纪》载武帝所祭之高里,并认为“蒿里”的产生是中国冥界观念的一大发展,即死人原来都在孤立的以家为中心的“聚落”,现在都要先到蒿里集合,构成了一个“社会”。吴荣曾也认为,蒿里即由高里讹变而来。汉人不仅相信泰山为鬼魂群聚之处,而且因为高里山和泰山相连,所以和泰山一样,被涂上神秘的色彩,把高里山也看作是和幽冥有关的地方。泰山为冥府中最高枢纽所在,而蒿里则是死人聚居的地方;前者相当于汉之都城,后者则相当于汉之乡里。余英时亦持此说。这自然是一种颇有见地的解释。笔者再作一些补充:蒿里还与后土信仰有关。《东汉光和五年(182)二月太原太守中山刘氏买田券》:“死人归蒿里戊己,地上地下,不得苛止。”《南朝宋元嘉九年(432)十一月都乡仁仪里王佛女买地券》:“归就后土蒿里”。均与后土联系在一起。传统文献亦有可征者,荀悦撰《汉纪》卷一四《孝武皇帝纪》:“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十有二月,襢蒿(高)里,祠后上(土)。”可知汉武帝之时即建有蒿里祠,并与后土同祀。
“蒿里丈人”在镇墓文、买地券中多称为“蒿里父老”,如《晋程氏葬父母镇墓券》、《武周延载元年伍松超买地券》等。也有称作“蒿里君”的,如《东汉初平四年(193)十二月王氏买镇墓文》。父老、丈人,皆乡间小吏,可见其身份并不高。《汉纪》所载官方祭祀者与蒿里丈人应该是同一尊神,但与泰山、上帝、后土等祭祀纪事并列,想必不会呼作父老之流,官方祭祀与民生宗教有别盖在于此。蒿里丈人虽“沉沦下僚”,但所执事权甚重,其所负使命为执行太上老君指令,斩杀妄图侵占墓地之鬼神。《南宋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袁州分宜县郭福寿坊彭氏念一娘买地券》:“切虑地中或有五方无道鬼神,妄有侵占。奉太上老君敕给地券一所,与亡人冥中自执为照。如有此色,即仰直圹大神收押,赴蒿里所司,准太上老君斩之。急急如律令。”
蒿里丈人是唯一可以确认其形象的墓葬神煞。据徐苹芳研究,他是明器之一,在《宋会要辑稿》所记永定陵中明器,即有蒿里老人。收入《永乐大典》的金元时期成书的《秘葬经》中,记天子至庶人墓中西北角,均置蒿里老公。南唐李升陵的后室发现一件老人俑,头戴风帽,脸有皱纹,颌下有长须,身穿圆领长袍,两手露出袖外,交迭于胸前,似持一带有圆柄物。李璟陵也发现一件,形制基本相同,只是下部残缺,双手笼于袖内。徐苹芳认为这些俑就是蒿里老人,但这只是推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西夏文物中找到了确证。1977年甘肃省武威县西郊林场西夏二号墓出土了一件蒿里老人图彩绘木板画。木板长28厘米,宽10.5厘米,画中人物头戴峨冠,身着交襟长衫,腰束带,拄竹杖。侧面墨书“蒿里老人”。虽然年代稍晚,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图像学数据。
(5)阡陌游击
“阡陌游击”,《熹平二年张叔敬镇墓文》称之为“冢中游击”,《东汉建和元年(147)十一月加氏妇镇墓文》中写作“伯(陌)上游徼”。游徼,秦汉乡官之一,掌一乡之巡察禁盗,《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游徼作为墓葬神煞,其职责应该是缉捕作奸犯科的恶鬼。在望都一号墓前室西壁绘有六人,其一榜题“门下游徼”,戴冠,持笏,衣袍宽大,袖垂及膝,面北弓腰而立,作朝拜状。与其同列者依榜题分别为□□掾、追鼓掾、门下史、门下贼曹、门下功曹,皆与门下游徼同负守护墓主责任之同僚也。
其它的神煞,我们只简略地提几句,不作详细考辨。墓典、墓录之属,均为掌管死人簿籍的文吏,犹《东汉延熹四年锺仲游妻墓券》之“主墓狱史”。墓鬼、墓耗,皆扰墓、害墓之恶鬼,祭之以示安抚,以免祸患。
总体来看,这些解注陶瓶多出土于简陋的墓中,主要反映的是汉代社会庶民的信仰。因此,我相信这些墓葬神煞原是流行于民间的方术杂迷信,后来被天师道所吸收,对早期道教的鬼神系统有一定的影响。《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分解冢讼墓注,……辄按《千二百官章仪》并正一真人所授南岳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为某家……加符告下某家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徼、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诸是地狱所典主者,并严加断绝某家冢讼之气,覆注之鬼。”张勋燎征引此节,云两相对照,可知镇墓文中讲到的鬼神名称,确与《千二百官章仪》等道书相合。虽然器文涉及的鬼神名目只是和解墓注有关的部分,远非当时鬼神名色的全部,却可说明道教中以天官和地官为主的三官鬼神系统其时已大体形成,非一般简单的民间巫术迷信所能有。其实,年代的先后颇不易论定,这些神煞的形成应早于道教,但有可能道教确立并不断组织化之后,又反馈作用于买地券和镇墓文。道教的起源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难题,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故不作过多的纠缠。
2、墓葬神煞传入敦煌年代蠡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敦煌佛爷庙、新店、祁家湾、三危山等地陆续发掘了一批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五谷陶瓶,上面均有墨书或朱书镇墓文。其基本形态有两种,现各取一典例,参考前人录文移录如下:
佛爷庙湾西凉墓葬M1:33陶罐文字:
庚子六年正月辛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身死,今下斗瓶□(铅)人五谷瓶,当重地上生人。青乌子告北辰,诏令死者自受其殃罚,不加尔移殃转咎,遂与他里。如律令。
同墓M1:34陶鉢文字:
庚子六年正月辛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薄命早终,算尽寿穷,时值八魁、九坎。今下斗瓶,用当重复,解天注、地注、人注、鬼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乐莫相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不得相□(注)。俟如律令。
谭蝉雪指出,青乌子乃汉代堪舆术士,相传着有《葬经》,“八魁、九坎”乃阴阳家之说。刘昭瑞将其与洛阳西郊东汉墓所出“解注文”进行比较,又引王利器《颜氏家训》卷二《集解》引《正统道藏.赤松子章历》所收《断亡人复连章》等材料对解、注二字作了新的释义。姜伯勤进一步细致考察,认为赤松子章历所载章奏,系按天师道教法上奏天曹,以闻太上与众真,以祈消灾度厄。文中“魁纲之鬼”,指触犯八魁九坎星煞之禁而带来灾殃的鬼害,“复注之气”,指给生人带来注病之气,这些都要请青乌子诏告北辰令,由北辰司马都官派官将来加以收捕。将此与上述镇墓文相印证,说明敦煌镇墓文出自方术,但其“厌解”之术,又为汉魏六朝的道教信仰所汲收。其中青乌子、星官之禁、注等说,均缘出于汉代之方术,亦即史实所称之“方仙道”。这些镇墓文反映了本地天师道与方仙道的融合。姜伯勤在此文中还将这些敦煌出土镇墓文按考古遗址编成系年表,标本号、年代、墓主、文献内容一目了然。王素等则将包括文献著录在内的全部甘肃所出镇墓文收入《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有全文录文、参考文献和简要的考订[96]。他们两位出色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检索便利。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自西晋咸宁二年(276)至北凉玄始十年(421),所有的镇墓文都可归属于上述两种类型,如果采用王素的广义的敦煌,则可将上限提至魏甘露二年(257)。也就是说,虽然汉代即有罗列我们上文所论墓葬神煞的镇墓文,但这种格式并没有传到敦煌。由于敦煌的古代墓葬尚未大规模发掘,我们缺乏晋唐之间数百年的考古数据。因文献不足征,目前不能断定这些墓葬神煞是何时传入敦煌的,我猜测很有可能要晚至唐初。
3、墓葬神煞的中国本土信仰特征
中国的墓葬神煞均出自本土信仰,但是也有少数显示出佛教的渗透,这主要表现在另一类性质的墓葬文献中。《北齐武平四年(580)七月高侨告神木牌》:
释迦文佛弟子高侨敢告:□湾里地振坦国土高侨元出冀州渤海郡,因宦仍居青州齐郡益都县渑□里。其妻王江妃,年七十七,遇患积稔,医疗无损,忽以今月六日命过寿终。上辞三光,下归蒿里。江妃生时十善持(持)心,五戒坚志,岁三月六,斋戒不阙。今为戒师藏公、山公等所使,与佛取花,往知(之)不返。江妃命终之时,天帝抱花候迎,精神大权,□往接侍灵魂。(勅)汝地下女青诏书五道大神、司之官,江妃所衣资杂物、随身之具,所径(经)之处,不得诃留。若有留诘,沙诃楼碎汝身首如阿梨树枝。来时,不知书读是谁。书者观世音,读者维摩大士。故移,急急如律令。
其中不少神祇出自佛教,如释迦、观世音、维摩诘,特别是将墓主王江妃之死因,解释成为佛取花,佛教的味道很浓,这是无可否认的。至于五道大神,成份比较复杂,原出中国固有信仰,即五道将军,后被佛教、道教吸收。但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中国本土的神,下勅的是天帝,传递诏书的是地下女青,执行者是五道大神、司之官。这一点又和买地券极为相似。
墓葬神煞在后世虽也有一些变化,但其基本体例却一直保留下来,未有大的改易,兹抄录一件明代买地券为证,《明景泰七年(1457)十月应天府江宁县金福满等为太监金英买地券》:
(前略)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备彩币,买地一方,东西一百二十步,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止朱凤,北止玄武。内方勾陈,分掌四域。丘丞墓伯,谨肃界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令具牲牢醴斋,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各已分付,令工匠修茔安厝,已后永保安吉。知见人岁月主,代保人令(今)日直符。故无(气)邪精,不得。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助葬主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券付亡过太监金英神魂收执,承(永)为照证。
墓葬神煞的持久“生命力”似乎远远超出民生宗教中其它类别的神祇,固然跟买地券、祭神文之类的程序化特质密切相关,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国人最看重的身后世界里,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基本没有触动,始终为本土神祇所牢牢占据。这也许是因为佛经中很少涉及到墓葬神鬼的缘故。吐鲁番的情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马雍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在高昌郡时期(327-442)的随葬衣物疏中,完全没有佛教术语,反映了民间的丧葬习俗仍然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为中国方术所主导。荣新江教授肯定了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申论,认为其中有些方术被后来的道教所吸收,但还不能把高昌郡时期的有关方术的资料都确定为道教性质。这种民生宗教中的部分内容的高度“凝固性”,十分耐人寻味,值得我们今后更深入地探究。
资料来源:摘录自互连网,谨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