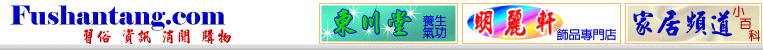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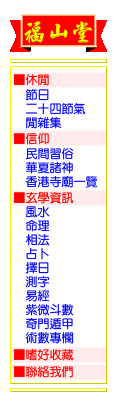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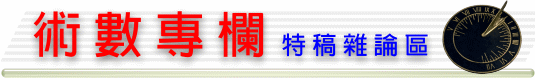
欽天監
官署名。掌管觀察天象,推算曆法。曆代多設置,名稱不同。周有太史,秦漢以後有太史令。隋設太史監,唐設太史局,後又改司天臺,隸祕書省。宋元有司天監,仍與太史局、太史並置。元又設有回回司天監。明清改名欽天監,設監正、監副等官。清制,漢滿並用,亦有個別歐洲傳教士參加。
各個朝代都有專事觀測的人。據《史記.天官書》記載:在上古,高辛氏以前有天文官重和黎,堯、舜、禹時期有羲氏與和氏;夏朝有昆吾;商朝有巫鹹;周代王室有史佚和萇弘,各諸侯國也都有自己的天文官……他們往往兼有神職,是帝王的特殊顧問。東漢時期,最高級別的天文官員稱作太史令,管轄天文臺和明堂兩個部門。具體主持天文臺工作的是靈臺丞,靈臺丞手下有四十二個助手,其中十四人觀測恒星,二人觀測太陽,三人測風向,十二人測晴雨,三人測時間,七人校驗鐘聲,還有一人叫做「舍人」,管一些雜事。總之,分工十分細致。元代以前天文機構的人員配製大體如此。元代的天文機構叫太史院。太史院下設三個局:推算局、測驗局和漏刻局,共七十人。明初的天文機構下設兩個分機構:司天監和回回司天監,後來司天監改稱欽天監,內設天文、漏刻、大統曆和回回曆四科,回回曆科不管編製回回曆法,而是把觀測推算結果提供給大統曆。回回司天監也改稱回回欽天監。在南京也有司天監和回回司天監,作為故都,人員和儀器配製與北京完全相同。
中國古代的天文機構具有皇家性質,太史令等天文官員,常常由皇帝親自任命。由於編製曆法和為皇帝占星是天文機構的兩項主要任務,所以天文學家和占星家有時就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天文官享有很多特權,比如清代的法律特別規定,欽天監官員犯罪要從輕判處。
古代的人們相信,凡是將要在人間發生的災難,上天都會通過天象的變化提前示警。從人類社會開始的那天起,就有了對天體現象的觀測。
古代埃及人是根據太陽和天狼星同時在地平線上的升起,來確定尼羅河的汛期;兩河流域即今日伊拉克境內最壯觀的建築物是觀察天象的塔臺即天文臺;而中國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象圖。因而,中國從夏、商、週一直到明清,都設有觀察天象、預測上天意志的部門和人員。
明代從事這項工作的是帶有一定神秘色彩的衙門稱欽天監。明初沿元代之舊,稱太史監,後改為太史監為太史院,再改名欽天監。為了探測上天的奧秘和意圖,欽天監在北京和南京的東南都建有觀象臺,臺上備有渾天儀、簡儀及其它設備。欽天監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掌察天文、定歷數及占候、推步等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諸天象,皆率其屬進行觀測,如有變異,則視為上天示警,得具奏疏密報皇帝。其術官有春、夏、中、秋、冬官正各一人,五官靈台郎八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漏刻博士六人。五官正主推算曆法、定四時,司曆、監候為其佐;靈台郎主辨日月星辰之 次、分野,以占候天象的變化;保章正專志天文的變化,以測定吉凶;挈壺正掌刻漏,以研求中星昏旦的位置;漏刻博士以漏定時,以牌換時,以鼓報更,以鐘鼓晨旦,司晨佐之。欽天監所置觀象臺,東、南、西、北四面各有四名天文生,輪番測候。
由於該監專業性強,故監官不得改任其他衙門,子孫世襲,不得改從他業。在監官員上自五官正、五官靈台郎、下至司曆、司晨、博士,以及天文生、陰陽人等,一方面要恪盡職守,觀察天象、修訂曆法,為大營建、大征討以及皇帝的冠婚、陵寢等選寶地、擇吉日,另一方面得不斷學習專業知識。在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中,天文曆法是最先進的領域。根據欽天監的觀察和各地奏疏,《明史》的《天文志》、《五行志》記載了大量有關太陽黑子活動、日食、月食、流星及流星雨、隕石及隕石雨、彗星、“天鼓鳴”及其他天體異常的現象。
自古以來,人類是敬畏天地的。沒有了天地,也就沒有了人類。太陽、月亮、白日、晝夜,山川,河流、花草、樹木,賦於了人類生存的環境。天地、四季、生物的運行決定了人類最基本的生活規律。源遠流長的文化告訴人類行為的準則。任何天體的變化和異常都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人類息息相關。
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
清初欽天監中的人事曾出現四次大規模的更動:頭一次發生於順治元年,在湯若望掌理監務之下,監中職官多改由天主教徒擔任,使用《大統曆》或《回回曆》的天文家均遭貶黜;第二次發生於康熙四年「曆獄」定讞前後,清政府在監中廣置滿洲監官員缺;第三次發生於康熙四年八月楊光先新任漢監正之後,習用西法的監員多遭剪除,楊光先並陸續考選了一批監官替補,初以《大統曆》推曆,後改用《回回曆》;第四次發生於康熙八年「曆獄」全面翻案之時,南懷仁率支持西法的天文家重掌監務,原監正楊光先及監副吳明烜等人均遭免官。這些人事上的大規模更張,多明顯為各不同民族或派別天文學在監中勢力消長的具體結果。
在滿人入關的前二十餘年間,監中一直未設滿洲及蒙古員缺。但由於使用《大統曆》與《回回曆》的天文家與使用西法的天主教天文家間,在清初屢起大獄,清政府為確實掌握並監督欽天監的運作,始於「曆獄」之初,廣在監中安插高階滿官,康熙九年,更開始著意培養基層的天文人才,並依其他衙門例在監中增設蒙古及漢軍員缺,而監中的漢人與西士自此轉型為技術官僚,從旁以其專業知識協助滿政權處理天文曆算及陰陽選擇等職事。
欽天監,為我國官署名,掌天文、氣象、曆法、推步諸事,占候日月星辰之變與風雲氣色之異。自唐以後,名稱屢易。唐代祕書省設祕書監,其下有二局:一曰著作局,一曰太史局,太史局即欽天監之前身也。周武后久視元年(西元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唐睿宗景雲元年(七一○),又改為太史監,嗣復稱太史局。至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三月十九日,勒改太史局為司天臺,是為單獨設制之始。並將臺址由長安子城祕書省西,遷至永寧坊東南。自此以後,置官較多,規模日增。設監一人,官秩為從三品(新唐書謂為正三品,我國過去官品有正從,猶言正副也),少監二人,靈臺郎二人,挈壺正二人,並設春、夏、秋、中五官正五人,皆為正五品,全臺正九品以上之官員,不下六十餘人。
宋時設司天監,仍襲前代舊制。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改稱為太史院。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復稱司天監。三年,改司天監為欽天監,欽天監之名自此始。官秩及組織,微有變更,職掌與唐宋二代無異。十四年,復改欽天監主管為正五品,設令一人,丞一人。二十二年,又改令為監正,丞為監副,以迄於清。
中國天文曆象之改進,甚得力於西方教士之來華,東來教士,多以天文學見稱於世。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採用西法開曆局於北京東長安街,以徐光啟督其事,西人鄧玉函、龍華民、羅雅穀等協同修曆,精密正確,所測無不合。
迨清人入關,續採西法,頒行天下,並任命湯若望、南懷仁入欽天監為官。南氏歿後,西方教士供職於欽天監者頗多,清代欽天監監正二人,常為滿人、西人各一,皆為正五品。左、右監副二人,盡用西人,官秩為正六品。五官正五人,從六品,皆為漢人。欽天監至民國始廢,其執掌由中央觀象臺司其事。
“外來和尚好念經” 湯若望獲重用之謎
欽天監,中國古代國家天文臺,承擔觀察天象、頒佈曆法的重任。欽天監正,相當於國家天文臺台長。由於曆法關係農時,加上古人相信天象改變和人事變更直接對應,欽天監正的地位十分重要。明代沿用的曆法計算方式誤差較大,不利於王朝的統治。恰在此時,傳教士帶來了斬曆法。
湯若望是繼利瑪竇之後又一個明清之際的著名傳教士。他是德國人,受葡萄牙耶酥會的派遣到中國傳教,明天啟二年(一六二)進人中國,取漢名湯若望。他有天文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崇禎三年(一六三○),徐光啟預備修訂新曆,將湯若望從西安調到北京,進入曆局成為徐光啟的助手。他不僅是天文學家,在機械製造方面也十分在行,幫助祟楨皇帝製造出威力強大的“紅夷大炮”,在對抗清軍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使得明、清雙方都將他當成不可多得的全能人才。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他在改朝換代的大動盪中堅持留在北京。六月,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城,命令城內居民搬出城外以安置大軍,湯若望上書請求保護,獲得清政府的優禮,他的教堂、三千卷書籍和為祟禎皇帝修訂的《崇禎曆書》刻板得到妥善安置。
清政府上臺,一項重要的工作是編制新曆法頒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曆。多爾袞命令欽天監官員負責新曆法的修訂。當時欽天監官員使用中國傳統的大統曆和回回曆,推算出天文現象出現的時間與實際發生時間差距較大,影響到新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多爾袞對此十分不滿,召見湯若望詢問有關技術問題。通過同年八月對日食時間的測定,三種曆法優劣頓現,漢、回曆法分別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測算結果絲毫不差。清政府當即宜布採用西洋新法,將新曆書賜名“時憲曆”,不久湯若望接任欽天監正,相當於國家天文臺的台長。能推算曆法的人在被當時被認為懂占星術,受到官員和民眾的崇拜。自湯若望以後,直到清道光年間,欽天監官員都用西方傳教士擔當。
湯若望獲得清朝統治者極大的尊崇,在中國受到如此禮遇的傳教士獨此一人。多爾袞極尊重他的意見,順治的生母也因為湯若望治好了自己侄女即順治皇帝未來皇后的病而感激之至。少年順治皇帝聽了太后和朝中大臣對這位西洋教士的褒揚,自然產生信賴感,更由於順治帝極強的求知欲,屢屢召湯若望進宮講解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兩人之間建立起超越尋常君臣之間的關係。順治帝稱湯若望為“瑪法”即滿語爺爺,順治八年(一六五一)一年之內,湯若望連升三次,從“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到“太常寺卿”,官級從五品升到正三品。順治十年(一六五三),賜給湯若望“通微教師”的尊號,地位,相當於國師。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湯若望獲贈“光祿大夫”的榮譽頭銜,官位升至正一品。不僅如此,順治帝還經常禦駕湯若望府邸,長時間暢談。這種做法被認為尊卑不分、有違禮教,激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滿。雖然如此,湯若望仍借助與順治皇帝的親近關係,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和行動的自由。
湯若望早在剛擔任欽天監正一職時,便在北京宜武門內建立了:一座歐式風格的雄偉教堂,參觀的人員絡繹不絕,順治十四年,順治皇帝禦筆親書“通微佳境”,製成匾額懸掛于宣武門的天主教堂,湯若望還把順治帝禦制碑文刻成石碑豎立在教堂前面。這一舉動等於默認了湯若望有自由傳教的權力。事實上,湯若望也經常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向皇帝灌輸基督教義,順治皇帝也閱讀了有關書籍。由於湯若望的聲望,中國境內的傳教士都得到了保護,入教的群眾竟達上萬人。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才二十四歲的皇帝因病去世,他的繼承人是年僅八歲的小皇帝康熙,宮內由祖母皇太后照料,朝中則由四位順命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鼇拜、遏必隆聯合執政,實權人物則只有鼇拜。隨著順治皇帝的去世,湯若望的地位每況愈下。首先是順治末年,一個略有小名的文人楊光先寫作《摘謬論》和《辟邪論》,投疏到禮部,分別攻擊西洋新法和基督教,在前書中,楊光先認為湯若望別有用心地用西洋曆法替代中國本土曆法,是蔑視大清的惡毒之舉,在後書中以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為參照系全面批駁基督教義。由於順治帝尚在世,禮部官員拒絕了楊光先的彈劾申請。傳教士一方于康熙三年由利類思創作(天學傳概),介紹天主教的產生及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反駁楊光先的指控。文中過分誇大基督教義的神聖,激化了矛盾。這時,湯若望中風病倒,由南懷仁代其履行公務。楊光先代表著反西方傳教士的一批人,包括儒士、回教徒等人,他們積極支持楊光先,使這一案件越來越複雜。
康熙三年秋到次年春天,朝廷公開審理此案,楊光先指控湯若望等人犯有三條大罪:陰謀叛逆、宣揚邪教和傳佈錯誤的天算學。長期審判的結果是,湯若望和欽天監七位官員被判處死刑,各地傳教土集中到北京接受審訊,拆毀全國教堂。但在審判的最後關頭,北京發生強烈地震,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太后直接幹預此案,湯若望和僕人才被釋放,五名中國官員仍被處死。不久湯若望病故,葬於利瑪竇墓旁,集中到北京的二十五名傳教士被驅逐出境。
楊光先就任欽天監監正。走馬上任後,他遇到曆法推算的技術問題,楊光先恢復大統曆和回回曆,結果當然錯誤百出。康熙年事稍長,不滿於鼇拜的專權,從欽天監人手追查。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春,康熙仿效乃父順治命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和楊光先實地測試,以辨優劣。經過幾次考查,楊光先敗下陣來,被革職,病死在回安徽老家的途中。
康熙皇帝恢復了湯若望的尊號,肯定了他的貢獻。南懷仁接任欽天監監正,經過這一重大曲折,中國天文學重新獲得了發展的機遇,以後歷任欽天監主要官員均為西方傳教士。傳教士在天文學上取得勝利,傳教的阻力卻越來越大,清政府對傳教活動的控制康熙中後期以後越來越緊,最終進入全面禁教階段。
資料來源:摘錄自互連網,謹供參攷。
![]()
